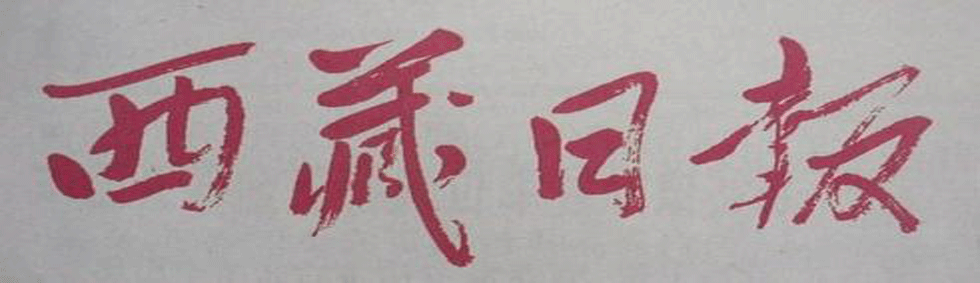
一个铺满黄金的山村
□王小忠
立春是个温暖的词,它总让人想到生长和希望。可对甘南而言,立春这个节气似乎徒有虚名,一直到清明时分,纷纷扬扬的大雪依然飘着。一点都不意外,甘南的四月如果不落雪,反倒让人心里不安。不知道江南的春天里有着怎样的柔情和含蓄,但我知道甘南的春天一如既往地被雪滋润着。立春这天,当我来到小小的偏狭的舟曲时,情况却不一样。十年前我曾来过舟曲,然而记忆却在不断增长的岁月里变得十分模糊。
舟曲是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县城,位于甘南州东南部,地处南秦岭山地,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区。白龙江像一条洁净的哈达,将整个县城分为两半。一条江在岁月里带走了荒凉与寂静,然后又带来了繁华与热闹。春天刚刚一到,江岸边的毛桃便挑起嫩嫩的幼芽,冬日里播种的麦苗也挺起娇羞的身段。这与相隔百里之外号称青藏屋檐的甘南州政府所在地合作市全然是两个无法对接起来的世界。感觉不到丝毫寒意,出发前的担忧和顾虑荡然无存。我们脱掉厚厚的棉衣,在县城吃过晚饭后,就直接去了黑峪沟。
山大沟深,是对僻远地区的惯性描述。车子行驶四十多分钟,之后,便进入崎岖山路。沿途不见人烟,只是黑魆魆的大山。转过十几个弯道,攀沿好几座高山,天已经黑透了,车灯照不了太远,行驶更加缓慢。透过车窗,我望见不远的半山上有灯火,那灯火星星点点,像是在眼前,又像是一群人提着灯笼在天边行走,时近时远,忽明忽亮。我忍不住问老王,他说这条沟就是黑峪沟,但距离我们要去的村子还有很长一段路。每年春节前夕,都要来这里,为村里群众书写对联。我问他,为何选择这山沟?他笑着说,因为这地方到处是“黄金”。接着他说起几年前的一段趣事。有同行的一个书法家准备给村里修建一个篮球场,便问他如何?他说,这地方找到一处能放兵乓球案子的地方就已经不容易了,建篮球场从何而谈呀。谁信呢?舟曲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难道就缺哪点地方吗?事实如此,舟曲人均占地还不到1.3亩,耕种之地更为罕缺。都说山大沟深,究竟大而深到何种程度?到村子你们就知道了。
老王说着无意,而我听着怎么也不相信。不知走到哪儿了,见不到天幕里的星辰,也看不见前方的道路。灯光照到十米之外,全然是挺拔的松树和耸立的高山。悬挂在松枝上的经幡,在夜风的吹刮下发出呼啦啦的声音。
转过这个山嘴就到了。老王见我们迷迷糊糊斜靠在座椅上,便说笑起来。沿江岸一直西行,穿过郎木寺,就是广袤无垠的玛曲草原。从海拔多米的高原抵达这里时,你就知道了,甘南不仅仅是冰天雪地,江南的柔情也并不缺少。我们一手掌着青藏的雪,一脚踩住水乡的温柔,何等狂放潇洒!山上大雪飞,山下稻米香,你说,还有啥不满足?我们听着都笑出声来。的确,人的不满足实在太多,那都是因为强求高于生活本身的一种欲望,对高于现状的渴求,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可谁能在一瞬间就战胜自己强大的欲求呢?
远远的,有人影晃动。这次真到了。老支书带领众人在村口等候我们。前前后后一行十余人,老支书连从来不用的挂在屋檐下的柏木小凳子都取了下来。大家围坐一起,几碗酥油茶下肚之后,旅途的疲惫随之消除殆尽。
熏腊肉是这里最具特色的食品,也只有客人来了才能品尝得到。熏腊肉在全国各地都有,但各有不同。羊肉要鲜吃,牛肉要风干,而猪肉则要熏透。猪是甘南特有的食坡地蕨麻而长大的猪,其肉肥瘦相加。大块大块的熏肉从厨房屋梁上卸下来,清洗干净,煮到锅里色泽金黄,烟香浓郁,吃一口肥而不腻,鲜美可口。
到藏区来,不端酒杯是说不过去的。藏族人的敬酒、喝酒也是一大特色。酒是自家青稞酿制的上等好酒,口感浓厚,入口甘醇。喝多了可麻烦,头脑虽说清晰,而双腿却不听使唤。因此,甘南人把舟曲青稞酒称之为“软腿大曲”。青稞酒因水质和发酵时间等略有区别,因而色泽也稍有不同,但大部分色微黄,酸中带甜。按照藏族习俗,客人来了,豪爽热情的主人要端起青稞酒壶,敬献客人三碗。藏族同胞劝酒时,经常要唱酒歌。敬酒歌种类很多,歌词丰富多彩,曲调优美动人。唱完祝酒歌,喝酒的人必须一饮而尽。月上树梢,而歌声依旧不断。其实大家都明白,到舟曲来喝不倒是不能入睡的。
天快亮的时候,我醒来了。外面没有声音,天空干干净净的,月亮高高挂在西边,星星稀稀疏疏,一颗一颗翻着跟头,然后跌入无边的虚空里。我再次醒来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没等洗簌完毕,就有人来叫。但凡一家来客,全村人都要轮流招呼。这似乎已经形成了这里的习俗。看着银碗里晃动着的青稞酒,双腿又无法克制地颤抖起来。歌声四起,那情形让人想起快意江湖,一碗碗甘醇的青稞酒下肚,便可仰天长啸,各个都成了诗人,恣意汪洋,无话不说。有人喝急了,大叫,这地方令人既爱又恨,如此喝法,岂不是土匪马贼!然而,当头发花白的老人双手端着酒碗,谁都不会拒绝。共和国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此厚实、自然、朴素的待客之道实为罕见。我们可以拒绝所有欲求,但不可以拒绝温暖和淳朴,何况这样的温暖和淳朴在短暂的一生里并不是时时都能遇到的。
我借方便之机悄悄走出屋门,发现这里人家都没有院墙,也无院门,几十层台阶的尽头便是屋门。下了台阶,便是出村、入户的小路。老人孩子都往村头的寺院赶去,有位老人说,今天是贡巴节,快到年关了,驱鬼祈福是不能少的。我知道这一带都属黑峪沟,但却不清楚这个村子的具体名字。老人说,黑峪沟是一个行政村,他们的祖先是吐番王朝的赞普派往边境东征的亲兵,来到了唐蕃交界的舟曲,由于西藏发生了叛乱,受到了唐朝军队和叛军的双重打击,所以才躲到了山大沟深的黑峪沟来。老人说完就走了,说是迟了赶不上法事活动。
我到老支书家去,老支书详细告诉我说,黑峪沟属于舟曲县憨班乡管辖,沟里有寺上村,黑峪村,兵马村,史称赛布斗,迈,卡上下三部。三个村子里都有寺院,寺上的叫黑峪寺,是藏传佛教,黑峪村和兵马村的寺院都称作贡巴寺,是苯教寺院。三个村子的寺院分别由各村村民供养,然而数百年来宗教活动却没有分开过。像晒佛节,香巴佛转寺,背经等,大致都为驱除瘟疫,祈福纳祥,给供奉他的庶民一个丰收的年景。
老支书接着又说,这里林很大,山头有护林员,他们轮流换班,有时候半年见不到人影。夏日有牧人深入峡谷,护林员只要望见,便扯开嗓子喝,喂,赶紧上来,要不我就不会说话了。他们也是人,但从不因为寂寞而放弃自己的责任。大家都知道护林员的辛苦,偶尔也有人送酒肉上去,肉照吃不误,而酒却点滴不沾。
我听老支书说完,心里突然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敬仰不已。快过年了,节日的味道整天就在我们身边缭绕,道路干净了许多,那些已怀孕的枝条满带着羞涩,山沟深处绿意隐约可见。黑峪沟藏语称为“塞布尔”,是金沙之峪的意思,地形成周峰环拱的狭长盆地,森林密布,山峦叠嶂,怪石凸悬,溪水澄澈,加之气候温润,不但能酿出上等好酒来,当然更是颐享天年的好地方。
鸟儿清脆的鸣叫已经很少听到了,哪怕是在乡村。老支书的家在村口,向下望去,是一条深不可测的山沟,抬头看见的便是直接云霄的大山,四周是叫不上名字的树木,鸟雀落满枝头,清脆的鸣叫声悦耳动听,它们选择在这里,把福音传递给村民,共同筑造着和谐而幸福的日子。我在村口的小路上来回走动着,突然被一串玉米吸引住了。玉米挂在木楼的二楼门口处,它们在光阴下的颜色更加纯真了。木楼非常古老,陈旧,主人是一位中年人,他见我望着玉米,笑着说,这是留给鸟儿的。大雪封山的时候,鸟儿们找不到食物,便会来这儿。几串玉米,剥下来也没有多少,留着便可以帮它们度过苦日子。我问他,玉米颗粒那么大,怕是吃不下去。他说,等下大雪了,就剥几个棒子,然后打碎,撒在地上。林里的鸟儿虽然个头大,胃口却很小。
这话说着无心,可听着却让人忍不住想起其他的事情来。鸟儿的胃口不随个头的大小而变化,可是人呢?人就不一样了。人的胃口往往大得无形,并不是因为生下来就那样,而是在生活中对于物质有了更高的追求,所以,平淡的日子很难满足日益膨胀的欲望。人的淡然之性全然被社会化快速的进程所打乱,在利益的驱使下,渐而丧失了本性,遗忘了道德观念。人是不能和鸟儿相比的,然而住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不一样,在我所走过的地方,真的还没有遇到过。没有院墙,也没有院门,某一家的客人,就是全村子的客人,这不是传说中的大同社会吗?
特大泥石流灾难的阴影还没有完全退出我的心灵,可当我走完这个村子的时候,根本看不到灾难曾莅临于此。他们各个满怀乐观,步步向前,在大山深处酿造着幸福的日子。对外界的侵扰不问不闻,把寸土视为金子,对森林的守护从不懈怠,将心灵所愿寄予桑烟之中,这样的平静与淡然,是身居都市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千百年来,他们酿着甘甜的青稞酒,吃着可口的山野菜,喝着山涧澄澈的泉水,过着世外桃源般的日子,这样平静和淡然的心态你能不羡慕吗?
随同的小胡在博物馆工作,他和我一样,喜欢在陈旧的木楼里出出进进。那天晚上,他取出一个木碗让我看。木碗估计已有好几十年了,不见木质的色泽,边缘处也略有开裂。
他告诉我说,是好东西。
我开玩笑说,你从哪儿偷来的?
他说,不是偷的,是人家给的。
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人家会轻易给你?
他说,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好东西。
我没说什么,但在心里却咒骂他不地道。后来我想,或许小胡做了一件好事情。白龙江流域辽阔、富饶,在漫长的远古时期,生活在这一带的戎族及后来分化的羌族先民们,为开拓生产,谋求幸福,同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从一草一木到今天的富丽华贵,我们可以从遗物中寻找先民们的生活状态、生产状况,乃至生活情趣。那木碗见证过一段不为人知的岁月,有一天在博物馆再次见到的时候,说不上真能从它身上找到更为珍贵的东西。不过我不敢保证,小胡会不会把它放到博物馆里去?
天还没有完全亮开,我就被小胡喊醒了。他说外面起雾了,非常美丽,像水墨画一样。我磨蹭了一阵,等起来时小胡已经不见影子了。雾慢慢散开了,山头树梢显得有点孤独,太阳的光芒越过它们,又像是去了天边。半山腰的雾气拥挤着向山下奔去,一会儿,几户人家渐渐露出屋顶,鸟儿的声音又鸣叫起来。我在距离村口不远的地方碰到小胡,他背着相机,手里拿着一对鹿角,笑嘻嘻地说,雾都散开了你才起来。我知道,他的目的不是拍照,而是去另外的一处木楼。何况那鹿角是另一处木楼里一位老人摆放在佛龛里的,我当时问过老人,说早年这里麋鹿很多,他去山里放牧捡到的,觉着好看,便带了回来,没想到让他盯上了。我拉着小胡去了木楼,执意让他给老人掏钱。小胡有点难为情,但还是去了。奇怪的是那位老人说啥也不收钱,说是随便捡的,也没啥用处。
从老人那儿出来的时候,小胡说,二楼上还有个纺车,人家当鸡窝呢。我说,你觉得有用的话也顺便拉走吧。小胡见我口气生硬,便不再开口。从中午一直到太阳落山,小胡没有出来,也没有去其他地方收集他所需要的东西,他在寺院门口的场地里整整写了一百多幅对联,也算是弥补了他的贪欲之心。
住了几日,我们就离开了黑峪沟。回来的路上,大家都不说话,车子在山道上小心翼翼地行走。金沙之峪,就算真的没有金沙,那有何妨?沟底的油菜在阳光下闪烁着绿油油的光泽,不过几日,这里便是金黄的世界。可是我想,当我再次踏进黑峪沟时,心里会想些什么?我用真实或者虚构的文字,记录着这里的一切,唯独找不到长久留下来的理由。我想,大概是因为贪念过盛,而早已看不到深埋着的黄金了。
多元包容纯粹诗意总第期
主编花盛
编委(按音序)阿垅阿信陈拓杜娟索木东李城李德全敏奇才敏彦文牧风王力王小忠扎西才让
合作媒体甘南日报羚城周末投稿邮箱gnwx.北京最权威看白癜风医院北京哪里治疗白癜风最好最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