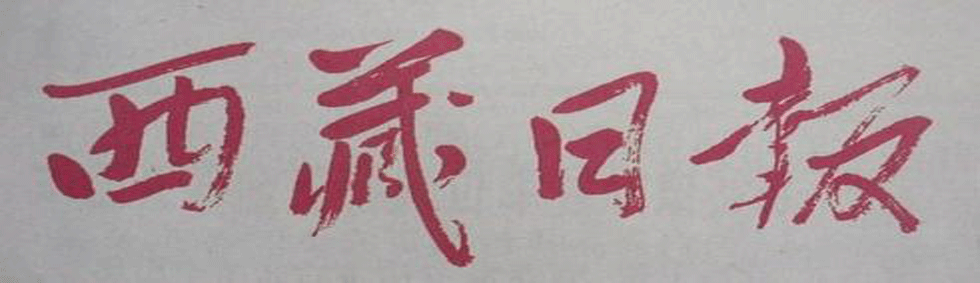
点击上方蓝字“边缘诗时代”一键
年生 活你是谁?你错认了家园大海上,一片落叶在漂泊做梦是一种清醒睁开眼睛,你不认识这个喧嚣的早晨阳光在叹息,它无法抺去大地脸上的皱纹某一种植物的液体哺育着奇迹、激情、狂欢和牺牲某一种野兽的毛孔里散发出阴谋和专制的气息你咬着牙抽动时间之鞭狠狠拷打爱情、欲望、野心和午夜的真相是什么悬浮在空中?久久不落下来?地上的人寸步难行在石头雕刻成的神像后面玩腻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一只猴子学会坐禅一块岩石学会像巫师一样跳舞谁的眸子里能找到天使的纯洁和柔情你低下头来,向一滴雨水举起双手雷电涌入你的躯体时你是否颤栗?相爱和仇恨都是漫长的苦役啊,人——戴上或者摘下面具歌唱或者流泪,生或者死阳光来临上帝的手指,掀开命运之书。谁读到了先知的谶语?像死亡一样不可抗拒像凯撒一样骄傲: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然而,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摔断腿的是你吗?在陷阱中挣扎的是你吗?天上——地下,幸福——痛苦爱——恨:天使的翅翼一半白一半黑来临的就让它来临吧尚未来临的:我们等待,我们祈祷但难道你不是一切吗?“不是一切!一粒灰尘也可以在天空称王”一棵草喊疼。一个被腰斩的梦喊疼一种纯洁在喊疼。大地在喊疼一缕不喊疼的风昂起头颅,我用我的伤口看见它那超现实主义的盘旋和俯冲吹进身体里面的风小时候,风能吹倒我的身体但吹不进身体里面去长大后,风吹不倒我的身体却能一点点吹进身体里面中年时,风吹进了骨头有时我听见骨头里飞沙走石的声音风正在一点点吹进我的灵魂等到灵魂灌满了风,我要在灵魂的壁上戳一个洞,“呼——”把自己的身体吹得杳无踪影会思想的鱼一大群先生女士,团团围住池塘个个神情严肃,像要对鱼们宣讲真理真理就是:我们要把你们钓上来,煮熟,吃掉乖乖上钩吧,用你们的献身精神换来我们的快乐和荣誉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钓鱼比赛,这些钓鱼者用谎言钓鱼钓累了,用面具钓鱼钓累了现在他们拿起真实的鱼竿小心翼翼装上鱼饵,把钩子甩进水里他们想:钓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鱼呀,是猝不及防还是勇于献身?浮子一晃,线突然绷紧钓鱼者的神经也突然绷紧拉线……起竿……鱼在钩子上挣扎绝望哭喊的是鱼,惊喜尖叫的是人我想象着:鱼点燃狼烟,放倒消息树或者吹起悲壮的号角……它们严阵以待这些会思想的鱼,是亚里士多德的化身“我决不给雅典第二次杀害哲学的机会”30分钟,60分钟……池塘边一群发呆的傻瓜!广场那些鸽子白得像是纸做的那些灰尘严肃得像是穿便衣的黄金那些飞得高高的风筝像是监视天空的特务那些光滑的大理石像一个个完美的阴谋那些石缝里残留的血迹像问号等待着注释那些吹来吹去的风像一群疯子集体逃离精神病院那些飘来飘去的阳光像是人人热爱的谎言那些遗忘,那些冷漠像洪水漫过广场……角落相对于“中心”而言,角落的地位等于一粒灰暗的泥土一粒泥土的呼喊和祈祷谁会俯下身来倾听?但一只野蜂的命运肯定比动物园的孔雀更富有戏剧性谁心甘情愿被冷落,被遗忘谁就赢得了自由热闹是一种病,孤独是最美的故乡。世界在疯狂地旋转你要抓住诗歌这个扶手在角落里站稳蚱蜢从这棵草跳到那棵草就好像人从青年跳到中年从中年跳到老年人跳得多么沉重,还要发出一些虚无主义的长吁短叹蚱蜢跳得多么轻盈,多么骄傲好像整个世界也在跟着它跳跃整个下午我躺在草地上呆呆地思考一个天大的问题——我要做一只蚱蜢呢还是做一个人?烛光不想熄灭太阳不想落山木槿花不想凋零沙滩上的字不想被海浪冲走云不想被风吹得杳无踪影雪不想融化一头双眼被闪电刺瞎的糜鹿不想坠入悬崖火车不想到站没电的手机不想沉默谜语不想被人猜出烛光不想熄灭做梦的人不想醒来一颗在空中剧烈燃烧的陨星不想在大气层中永远消失一封信不想被撕碎一首诗不想结尾一道射出的目光不想收回一滴泪水不想掉下来一杯酒不想被洒在地上一座荒芜的古寨不想让所有的往事被遗忘掩埋看 夜看他黝黑的皮肤,看他光洁的额头看他的衣服上缀着灯的纽扣——看他闪闪烁烁的虚荣看他的血液,看他的骨头用第三只眼睛看他的秘密——看他躲躲藏藏的欲望看他伸向四面八方的手抓住了怎样的风和雨,喜剧和悲剧看他庇护什么,出卖什么看他用黑暗涂抹一切的时候他脸上堆积的轻蔑和狂妄看他空虚的灵魂在天地间无休无止地膨胀看这个黑乎乎的气球升得多高,飘得多远看气球爆炸的时候那些碎片击中多少做梦的孩子!大风它疯狂地攫取是为了痛快地毁灭它抚摸了谁是为了彻底地抛弃谁它把谁举到空中是为了狠狠地砸下来它发出歇斯底里的嗥叫是为了吞噬宇宙间所有声音它隐藏自己的身影是为了让它的对手来不及隐藏它闪电般发起攻击是为了让自己闪电般溜走它把世界搅得天昏地暗是为了自己能够横冲直撞它威风凛凛时仿佛比整个世界还要强大它穷途末路时吹不动一只蚂蚁一片皂荚树叶动了一下无风的下午一片皂荚树上的叶子突然动了一下就这么一下它再也不动了它周围的伙伴一动也没动过没有风它们不敢动甚至不敢起动一下的念头但它动了一下它动了一下风却不敢动了某一个瞬间整个世界似乎都不敢动了伊甸年出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童年和一部分少年时代在桐乡与吴兴县接壤的一个名叫李家坝的小村度过,曾经拔秧、割稻、耙地、锄草。后来去海宁硖石镇上学、做工、教书,年移居嘉兴,现任教于嘉兴学院,教学生写文章。出版诗集《石头?剪子?布》,散文集《疼痛和仰望》、《别挡住我的太阳光》,小说集《铁罐》。一30years见证诗歌的力量八十年代:那些深深的记忆伊甸三件影响我整整一生的大事,拉开了我的八十年代的帷幕。第一件事情是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交,我恋爱了七年的女朋友突然离开了我。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的是她恼火的声音:“你一天到晚写诗,写诗,写出了什么名堂啊?”是啊,我写诗,写诗,写了好几年连一首诗也没发表过。七年了,我已习惯了这恋爱,习惯了反反复复的争吵,和好,争吵……当我明白这次不是一般的争吵,而是她决心要离我而去时,我似乎感到天要塌下来了。我赶到她居住的小镇,企图挽救这段恋情,我的几个朋友知道后,也专门赶来劝她……但,她离去的步伐是如此坚定。这第二件事情紧跟着第一件事情:五个月后,我在年6月号《东海》发表了处女作,一首总共只有四行的小诗,题目是《杨花》,内容是对她的谴责——若干年后,我为此谴责自己并向她写信道歉。人家爱不爱我是人家的自由,我有什么权利谴责她?况且,应该被谴责的是我,一个26周岁的女孩,跟我恋爱了七年,我却没有能力娶她,虽然穷不是我的罪过,但我确实对不起她,她离开我是对的。二十多年后,我在一首题为《石门镇》的诗中写道:我抚摸过的手臂越来越凉正如入秋后那段弯曲的运河旧轮船码头的一级级石阶摇摆着冷飕飕的尾巴钻入水底临河小客栈,一个落魄书生遗失的《警世通言》,化作片片暮色飞出窗外缘缘堂,堰桥浜,沈家弄,南皋桥……比爱和恨更长久的是什么?…………发表处女作标志着我的一段新生命的开始。我从年开始投稿,虽然两年以后才发表处女作,但我一直得到了编辑的热情鼓励和耐心指导。当时《东海》杂志的诗歌编辑是一个年轻人叫陈建军(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曾经一句一句地修改我的诗),《江南》的诗歌编辑是一位老诗人叫张往。我在年8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全省诗歌创作会议在莫干山召开,今天上午我去省作协报到,见到了热情的长者张往老师。张往老师在编辑《江南》诗歌的时期,对我有过很热烈的支持,现在也常常帮助我。晚宿民航招待所。在这里首次见到了陈建军。年我刚开始投稿时,是他给了我信心和勇气,后来龙彼德和张往等老师对我的重视,也得益于他的推荐……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关心过我、帮助过我的人,我都不会忘记。年伊甸在西双版纳第三件大事是:我正式成为海宁二中的一名高中老师,至此开始了我此后直到退休为止长达三十多年的教师生涯。这是我十分热爱的职业,与那些纯真清澈的灵魂打交道,这是最有诗意的事情。我一生中最没有遗憾的两件事就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能与学生相伴,与文学相伴。海宁二中在一个冷清的小镇——袁花镇上,但我从未感到寂寞和空虚过。特别刚到二中的时候,备课,上课,批作业,做班主任,忙得团团转,但我给自己规定:每周六下午和晚上必须写诗。每天必须抽出时间看书。我从每月四十几元的微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钱来买书和订杂志,最多时订了十七份报刊,有《青春》《萌芽》《诗刊》《星星诗刊》《青年文学》《外国文学报道》《文论报》以及几份语文教学杂志。然而,写作的步伐如此艰难。从年到年,我写了几百首诗,自己刻钢板油印了几本诗集,但在报刊上发表的一共只有二十几首诗。管收发信件的那位老师忍不住问我:“怎么都是退稿?”说得我脸都红了。这二十几首诗,主要发表在《东海》《南湖》和《浙江日报》上,我至今常怀着感恩的心情想起那几位给我带来鼓励的编辑老师。《东海》的诗歌编辑龙彼德老师在发了我的处女作以后,紧接着在下一期《东海》又发表了我两首短诗。他还两次不厌其烦地跑到海宁来看我,当面指导我的写作。我那时还很不懂人情世故,居然没请他吃一顿饭!我在年1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新年第一天是吉利的。《东海》的诗歌编辑龙彼德老师像吉祥的天使飞临了硖石——专门为我飞来的。他告诉我:我是他们的重点作者……龙老师就我的《追求》(油印诗集)在思想上艺术上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南湖》的诗歌编辑是黄亚洲,他远远地跑到袁花来看我——那时候的交通是何等不便。当时《南湖》的编辑部在湖州,他坐两三个小时的汽车到杭州,又从杭州坐三个多小时的汽车到袁花。回去时,他要坐一个小时的汽车到硖石,再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到嘉兴,从嘉兴火车站走半个小时到汽车站,再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到湖州,路上差不多要折腾整整一天。在海宁二中我那简陋的宿舍里,,我们相谈甚欢。我在宿舍里的煤油炉上烧了一个蛋花汤,去食堂买了几两饭,就算是招待他了。《浙江日报》的副刊编辑马瑛瑛,刚刚大学毕业,充满精力和热情,她不仅发表了我的诗歌,还让我去普陀山参加报社举办的笔会。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几天,一个杭州老朋友给我发来了他一直珍藏的我发表在年3月25日《浙江日报》上的小诗——《黎明的印象》:“哦,黎明竟是这样美好!/一片薄光,好似刚刚在玫瑰花液里浸过。/天空和大地,/涂上了一层鲜嫩而透明的红色。/东方,金色的希望之树,/伸出千万条枝干在空中摇曳,/轻轻撒落无数的花骨朵……”继龙彼德之后担任《东海》诗歌编辑的有楼奕林、方跃(楼奕林后来调入《江南》),每次我寄稿子去,无论发表还是不发表,他们总是耐心地给我写回信。他们的回信,我全都珍藏着;他们的热诚我也一直珍藏于内心深处。楼奕林做诗歌编辑的时间最长,从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我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她寄稿子,不知道给她带来了多少麻烦。她是我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发表我的作品最多的编辑。我之所以对她特别敬重,除了她三十年一以贯之的对我的热情鼓励和扶持之外,她人格上的善良、纯粹、嫉恶如仇更是我从内心里敬佩有加的。后来,《文学青年》的诗歌编辑叶坪、《文学港》的诗歌编辑力虹,都从最初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渐渐地变成了好朋友的关系。八十年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编辑们对工作、对文学、对作者那种阳光般澄澈而明亮的热情,真是温暖人心啊!而且,八十年代的编辑大多有两个特点:其一,稿子用或不用,都会不厌其烦地写回信。他们在回信中常常会先鼓励一下作者,然后提出建议。在“一片树叶掉下来会砸在三个诗人头上”的八十年代,一个诗歌编辑一天得写多少信啊!如果当时的编辑对我都很冷漠,我怀疑自己有没有信心写下去。其二,编辑对待作者大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姐妹那样,亲切,真诚,对作者只知道付出,不求回报。我当时既不请编辑吃饭,又不给编辑送礼,反而是我到编辑部拜访编辑时,他们请我吃饭,给予我各种帮助。杭州建德路九号——一个难以忘记的地名,在省作家协会的食堂里,我吃过几次饭,现在已经想不起是哪位编辑招待我了。年四月的某一天,《诗刊》编辑王燕生老师在北京团结湖附近的家里请我吃饭,喝酒;那年十月我和妻子旅行结婚经过成都,《星星》诗刊编辑鄢家发请我们吃十三道成都名小吃,《星星》元老蓝疆老师借给我两百元钱。年暑假,在我和朋友沈健闯荡大西北的路上,更是得到了不少编辑的热诚款待。西安《长安》杂志诗歌编辑子页请我们吃羊肉泡馍;兰州《飞天》诗歌编辑张书绅老师、李老乡老师请我和沈健吃兰州拉面;西藏《拉萨河》杂志编辑洋滔知道我有高原反应,专门到旅馆里来看我,给我送来好几瓶水果罐头;石河子《绿风诗刊》编辑李春华借给沈健两百元钱;《伊犁河》编辑顾丁昆让我们吃住在他家,还陪着我们到维吾尔和哈萨克诗人家里过古尔邦节(最近见到伊犁诗人亚楠,才知道顾丁昆不久前因病去世,心里一阵抽紧,29年前和他在一起的一幕幕情景如此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在诗歌编辑中,我特别难忘的是《诗刊》的王燕生老师和《十月》的骆一禾。我最初在《诗刊》发表的几组诗,都是寄给邵燕祥老师的,但最后是燕生老师选的稿,是他给我写的信。无法想像,当时他每天要写出多少封信,我想,燕生老师可能是八十年代全中国写信最多的人。我珍藏着他写给我的十几封信,虽然每封信都很短,但字里行间的热情和诚恳每每让人感动。他不仅鼓励我,也坦率地指出我的不足,让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比如他在年4月26日给我的信中提醒我,写诗“宜写出丝尽而化为蛹的或分娩的那种痛苦”,“我的意思是要加重,不宜过轻,这就应更趋于内向,而不在于急于向人们展示什么”。我读了这封信后,对诗歌的“重”与“轻”的问题认真思考了一段时间,后来我的诗作中那种过于轻盈、轻飘、轻浮的东西便越来越少了。年我参加第六届青春诗会,他是我的指导老师。在我的记忆中,每次见面,他总是在微笑。他见到任何一个作者总是微笑,仿佛所有年轻的作者都是他的孩子。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天,我,力虹,沈泽宜老师和一个女孩陪燕生老师逛乌镇,那天晚上,我们在乌镇街头散步,那位可爱的女孩一手拉着白发苍苍的燕生老师,一手拉着步履蹀躞的沈泽宜老师……像一个善良的天使代表上帝来看望两位内心充满诗意的老人——这情景,像一幅色彩鲜明的油画一直映现在我的脑海中。现在,两位老诗人都已进入天堂,愿他们在天堂经常有天使拉着他们的手悠哉游哉地散步。骆一禾和西川、海子在八十年代被称为“北大三剑客”。年他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十月》杂志做诗歌编辑。海子在年3月26日卧轨自杀以后,骆一禾在悲伤中整理海子的遗作并接连写了好几篇有关海子的文章,想不到两个月后,他追随海子而去(5月31日死于脑溢血)。年,我曾经给骆一禾寄过两次诗稿,他给我写了三封信,其中有两封居然密密麻麻长达七页。他在信中侃侃而谈,从宗教到哲学,从《奥义书》到《老子》,从朦胧诗到超现实主义,他旁征博引,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左右逢源。他的信充溢着智慧、学识、灵气和激情。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真挚、热忱、敬业的编辑。也许他的聪明才智全都发挥在文字上了,我们见面的交谈反而显得平静和平淡,没留下深刻印象,只记得他有点瘦,有点年轻,有点英俊,有点不修边幅。他的字迹纤细秀丽,像是女孩子写的,他的细心和温柔也像女孩子,但是他的诗歌却显示出比男子汉更男子汉的气概:“伟大的幻想 伟大的激情/都只属于个人/随生而来 随生而去/每一个世纪都有人摸索它 由此竭尽/哪一首血写的诗不是热血自焚”。骆一禾的死实在出人意外,他匆匆离开世界时才27岁啊!那天,阳光如此热烈,就好像是从成千上万人的血管里流出来似的,骆一禾的灵魂就在这阳光里融化了。年的海子和骆一禾,是上帝悲悯的眼睛里流出的两滴澄澈的泪水。骆一禾给我的两封长信,是我几十年的投稿经历中,编辑写给我的最长的信,几乎等同于两篇诗学论文。我在这里摘录一部分:两组诗都收到了,对于后来的—组,我觉得在运语造句上要浓厚斑斓些,总体上却不及长诗那样开阔富含……在《柔软的钟表》里,变形的造诣当然是够有力的,然而在发现新原型,作为世界观(审美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新生的发掘上,却还不够;因而也就和其它说法也能把握的原型相近。换—种说法是不够的。《柔软的钟表》将诗意的基础建立在一种表象变形上,如大街断裂如鰐鱼,牛首人身,黑皮鞋与白皮鞋引起的“白狮子”的视象感等等,反而对于时空与内心世界的、引起了形变——或“非常道”的真——的动能,失去了认识和诗化,停留在表象的结果上,反与起源隔膜了。例如在《投信》一首里,那种神秘的力量倒是应该把握的,或如《四面八方有眼睛看着我》倒是写得好的。又如《荒唐的大桥》,它的荒唐的力量为何,而不是它因为有“荒唐”而躲闪这一形变,是更应把握的。你的长诗《献给爱情的十个花圈》,我觉得比《柔软的钟表》为好,它较为深入,虽然对于这种深入的表现不及《柔软的钟表》斑斓。这首诗你花力气再弄一下是值得的。骆一禾在给我写信的时候,我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他的信是寄到鲁迅文学院来的,而且他在信里说过几天就会来鲁院看我,信里的这些话,他完全可以当面和我说,但他还是选择了写信这种方式。骆一禾的三封信,28年来我一直作为宝贵的资料珍藏着,前几年我把他的两封长信在我主编的民间诗刊《远方》上登载了出来。常常,因为某一个词,某一行诗,某一处景,某一缕思绪,我会突然想起骆一禾。我写过这样一首诗——《想起骆一禾》:“今天不是清明,也不是你的祭日/我独自坐在一个小小的湖泊边上/突然想起了你。这时一列火车从两百米外/没心没肺地驶过/天空开始用它的忧郁涂染大地/我毫无理由地想起了你/想起你湖水般清亮的表情/你女孩子一样温柔的笔迹/你先知般热烈而神秘的诗歌/但我想啊想,想不起你的声音/像猫一样忧伤还是像牛一样浑厚/或者像荆棘鸟一样美丽而惨烈/……这时被染黑的湖水向天空倒灌/最亮的几颗星星在孤独中颤抖/我突然不想你了——你是追逐阳光而去的/我怎能用黑夜来想你?”随着八十年代的消逝,那种沾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也渐去渐远,虽然后来我还是遇到过不少热心真诚的编辑,但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的编辑都把作者当做朋友的那种热情,后来是很难感受到了。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两件出乎意料的事彻底结束了我幸运的、天真的八十年代。一件事是好朋友方向的自杀。方向是我湖州师专时的同学(虽然我年龄比他大得多,但论资排辈,他算是我的师兄,我是做老师后再进湖州师专进修的),我们都酷爱诗歌,因此一见面就成了好朋友。他毕业时本来可以留校,因为在校期间谈恋爱的缘故,被取消留校资格,打回老家千岛湖,起先在县政府工作,后来到淳安县文联做秘书长。因为来自于爱情和现实的双重打击,方向于年10月19日在自己的宿舍里服毒自杀。他自杀前一年,他的诗艺已有突破性的进展,他的这首《出神》,可视为当代诗歌中的经典之作:“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作成我的诗歌……我看到好的雨落到秧田里/我就赞美;看到石头/无知无识,我就默默流泪//我说话,我干活,我行走,劳动生产/热爱诗歌。不骄傲/也不谦虚;不平静,也不喧哗/向空中撒种,在地上收获//在农闲季节埋头写作,看窗外的风景/痴痴地出神。”方向自杀一个月后,我、沈健和沈泽宜老师结伴去千岛湖畔他的墓地悼念他。他的墓碑上刻着他的一句遗言:“想写一首诗。”回来以后,我写了一首一百多行的诗《横卧山野的红玉米》纪念他:“谁听见红玉米内心的祷祝?/想写一首诗?用闪电和流星的笔才能入木三分/入金三分,入水火土无限深度……红玉米,横卧山野的红玉米/我看见你的嘴唇翕动,焦裂的嘴唇翕动/你想诉说什么?/风暴在头顶掠过,世界的耳朵从树上纷纷坠落/只有我一个人张开全身的伤口/作痛苦的倾听”。第二件事是我遇到了一个骗子——这样的事情在八十年代几乎不可能发生。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有人来敲我家的门,他说他是四川的宋炜。当时,四川宋氏两兄弟(宋渠、宋炜)在诗歌界赫赫有名。我连忙把他引进自己家里,好菜好酒地招待了他两天。第三天深夜,我突然发现抽屉里少了五十元钱,我马上想到他不可能是真正的宋炜,一个在诗歌界已有一定名声的人,怎么会为五十元钱而甘冒名誉被毁的危险呢?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不是宋炜!”他眼睛眨巴眨巴的,知道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他偷去的五十元钱,我谴责了他,然后把他赶走了。翌日上午八点,我赶到嘉兴市文联,对刚刚上班的余华等人说了这件事,他们认为诗人才会那么傻,那么容易受骗。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刚离开文联,那个骗子就把电话打到了文联,余华接的电话。那人说他是四川诗人宋渠,来浙江组稿。余华冷笑着说:“你再去找伊甸吧!”就这样,忧伤和荒谬这一对兄弟为我拉开了九十年代的序幕。我彻底告别了我的浪漫主义的八十年代。年诗友合影:伊甸、柯平、力虹年柯平在盐城作诗歌讲座我相信诗歌对人性的滋润……伊
甸1、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伊甸:20世纪80年代确实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年,当时我已从大学毕业,在一个浙江省作家协会组织的文学活动中,与杭州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交流,记得当时杭大几乎每个系都有诗社,每个班都有痴迷于诗歌的狂热分子。整个80年代,中国所有大学里都有无数热爱诗歌的学生。舒婷、北岛、顾城年在四川跟大学生见面,被几千个狂热的大学生包围着索取签名,以至于舒婷恨恨地说:“这些大学生全是暴徒!”一批诗歌的狂热暴徒啊!这一切在年戛然而止……9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以逃避虎狼般的速度逃离诗歌。此后,舒婷、北岛、顾城们再无可能遇到大学生的狂热包围,代替他们的是一夜暴富的企业家和一夜窜红的影视明星。2、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过程(大学期间创作、发表、获奖及其他情况)。伊甸:这个问题原来是“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我把“革命生涯”改成了“过程”。虽然我知道提问者不过想让问题稍微有趣一点而已,但我实在不喜欢“革命”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它既定的色彩,况且它的意义过于含混不清,我没有听任何人清晰地解说过这个词的明确含义,所以我从来不使用这个词。很惭愧,在某种意义上,我是“混进”大学生诗人队伍的。我比当时“正宗”大学生诗人年长10岁左右。我是做了中学老师后再考入湖州师专(现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在进入湖州师专之前,我只发表过十几首诗。年我进入湖州师专后,跟各地大学生诗人交流甚多,受到当时大学生诗风的影响,创作上口语化、生活化的现象特别明显。年在邵燕祥老师、王燕生老师的支持下,6月号《诗刊》以《诗二组》的形式发表了我的十几首写工人生活的诗(文革中我在海宁化肥厂做过多年司炉工)。紧接着在《飞天》、《星星》、《青年文学》、《萌芽》、《青春》、《诗歌报》等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诗歌。曾经获得《飞天》大学生诗歌奖、《萌芽》文学奖、《绿风》诗歌奖以及各种诗赛的一二三等奖。当时自然是十分兴奋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诗大部分都很表面化、概念化,是肤浅和幼稚的。3、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伊甸:首先是狂热地写诗。我在湖州师专读书的两年时光几乎都用来读诗和写诗了。然后与各地大学生诗人频繁通信。4、您当年的代表作是什么?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伊甸:惭愧,实在找不出所谓的“代表作”。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未名诗丛”(主编朱先树,责任编辑王燕生),我的那本《红帆船》中的二十二首诗,可以代表我大学生时代的诗风,比如《我永远年轻》、《幻想号》、《佩带木槿花的小村》、《站台》等等,大多有一种虚张声势的浪漫主义激情。5、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伊甸:年,高校的气氛比以前宽松了一些(此前由全国十三个最好的大学中文系学生联合创办的文学杂志《这一代》被禁。大学生自发成立文学社和诗社往往被认为不合法),我的一位朋友,当年留校做了湖州师专团委书记的杨柳先生告诉我,上面支持学生组织文学社团了,于是我们马上成立了一个诗社,取名“远方”。我担任了第一任社长。姜维扬、乔延凤编的《诗歌报》、洋滔编的《拉萨河》曾发表过“远方”诗社的诗歌专辑。整整三十前过去了,“远方”诗社仍存在,今年5月在远方诗社一直以来的指导老师沈泽宜先生(诗人、评论家,年在北大中文系被打成右派)的倡导下,由湖州师范学院出面举办了远方诗社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6、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伊甸:“远方”诗社刚创办时,我们每学期编印一本油印的《远方诗刊》,主编沈健(现在是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诗歌评论家)。第一二三期《远方诗刊》油印本我至今仍珍藏着。几年前,在沈泽宜老师一些热爱诗歌的弟子的资助下,出版了新的《远方诗刊》,最近出了第四期。第一二期由我和邹汉明任责任编辑,第三四期由我一个人任责任编辑。现在的《远方诗刊》是一本面向全国诗坛的民间诗刊。7、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伊甸:当年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学生诗社大多是名牌大学的诗社,我所在的学校是一个地区级的师专,但我们的远方诗社在大学生诗坛的影响直逼名牌大学的诗社。当年远方诗社有好几位社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诗歌。我们举办过各种诗歌朗诵会、讨论会。记得有一次是在湖州附近的山上举办篝火朗诵会,每一个人都要朗诵,然后由大家投票选出获奖者。我朗诵了北岛的《一切》,社员们一则抬举我这个社长,二则可能是因为喜欢北岛的诗,把我五音不全的朗诵评了个奖,奖品是一个笔记本。8、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啊?伊甸:当年囊中羞涩,很少出去串联。只有一次,刘波在湖南株州要举办一个全国青年文学社团联络会议,年四月底,我和柯平来到株洲,才知道这个会议已在团中央的干涉下被取消。据刘波说,他已经向所有被邀请的人发去会议停办的通知。但一些人没收到这个通知,仍然赶到了株洲,除了我和柯平外,还有廖亦武、潘洗尘、冯晏等。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场年轻诗友的自由聚会,比正儿八经的会议更让人难忘。潘洗尘是我第一个见到的外地大学生诗友,这几年联系不少,他编的杂志好几次发表了我的作品,他编的EMS周刊出了一本《伊甸新作快递·阳光总是走得很慢》。很感谢他的热情。但株洲见面以后,29年未曾见过面,去年夏天我在大理也没找到他的人影,今年夏天我还去大理避暑,他的读诗吧可能会是我常去的地方。年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见到了苏历铭和华海庆,匆匆相见,未及深谈。这几年通过微博、
9、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啊?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伊甸:当年和我通过信的大学生诗友有:苏历铭、潘洗尘、程宝林、朱凌波、华海庆、杨川庆、包临轩、杨榴红、吕贵品、燕晓冬、尚仲敏、许德民、卓松盛、张小波、陈鸣华、傅亮、沈国清、张洪海、黄灿然……他们分别来自人民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湘潭大学、南京师大、暨南大学等全国各地的大学。当年通过信的大学生诗友起码有50位以上,这些诗友中我只见过一小部分,但即使很多诗友从未见过面,80年代的通信让我们彼此有了了解,有了友情,一见面就会像碰到熟悉的老朋友那样亲切。80年代的所有信件我全都保存着,如果哪位诗友怀旧时想看看自己当年的笔迹,我可以复印了寄过来。如果哪位诗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了他的纪念馆,我愿意把他写给我的信全部捐献出来。情书这种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它属于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秘密,回避了吧。10、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伊甸:实际上,现在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人,除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派诗人之外,大多是80年代的大学生诗人,只不过有的是80年代初期和中期毕业的,有的是80年代末毕业的。80年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和90年代以及本世纪毕业的大学生在理想、责任感、忧患意识、人生境界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80年代的大学生诗人是王家新。当年我从一本好不容易借到的《这一代》上看到了王家新的两首诗,尽管没抄下来,但记忆非常深刻。其中一首诗写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窗帘是拉上的,车里的官员(当时只有很高级别的官员才有资格坐轿车)与车外的群众是隔膜的;另一首诗写鸟儿可以从某座桥上飞过,但普通人却不可以从那座桥上走过。王家新写这两首诗的时候,还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的诗里所呈现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即使放到三十多年以后也还是非常宝贵的。还有吕贵品的诗,虽然也有着口语化、生活化的大学生诗歌的痕迹,但他的诗是深沉的,他通过对一些细节的描述呈现出思想的力量。但吕贵品的这些诗歌,很可能是大学毕业以后写出来的。年伊甸与台湾诗人管管在西湖边年5月漓江上诗人们合影11、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学生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您还有印象吗?伊甸:印象较深的有华东师大的《夏雨岛》,复旦大学的《诗耕地》、燕晓冬、尚仲敏的《大学生诗报》。应该还有湘潭大学的《旋梯诗刊》,吉林大学的《北极星》、潘洗尘的《北斗》、黄灿然的《红土诗抄》、浙师大的《黄金时代》等等,等等,可惜我记性太差,大多不记得了。当年大学毕业时把那些没有任何价值的教材、一些随时可以买到的书搬了回来,却没把这些越来越显得珍贵的大学生诗歌报刊搬回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实在太愚蠢。12、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伊甸: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正是跟整个社会的理想主义密切呼应的。它的激情,它的纯粹,它的天真——都是非常珍贵的,但是它就像一个美丽却脆弱的瓷器,在八十年代末严峻的现实面前砰的一下碎掉了。九十年代,大学生的整体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实主义、功利主义成为大学生中占主导地位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要让大学生重新回到80年代那种激情、纯粹、天真的状态,看来是不可能了。它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怀旧的风景。但它仍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是:80年代的大学生诗人现在虽然已进入中年甚至老年,但他们的灵魂深处,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那种诗意的东西仍在发出光芒,使他们多多少少避开了势利、狡狯、邪恶。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这个时代,纯粹和天真越来越成为稀罕之物,势利和狡狯越来越大行其道,80年代的大学生诗人也难免有一些人渐渐学会了见风使舵,学会了唯利是图,学会了尔虞我诈,但这肯定是少数,这样的人当初对诗歌的热爱不会是出自内心的,不会是一种别无选择的生命需要。总体上,我相信诗歌对人性的滋润,我相信诗歌对热爱它的人带来的对邪恶和虚伪的免疫力。13、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伊甸: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让我发现,中国有那么多热爱诗歌的人,有那么多纯粹和天真的人,有那么多灵魂在发出光芒的人。即使在对现实和未来感到绝望和沮丧时,我还是能透过大片雾霾和黑暗看到这些光芒。我最大的收获是,当我沉浸在诗歌中、当我沉浸在和诗友们的灵魂交流中,我对世界之美,对人性之美就有了信心。我感到了生命中诗性的存在——那是活着的唯一意义。我最美好的回忆就是那些诗歌,那些像诗歌一样的信,那些像诗歌一样的灵魂。14、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伊甸:正好你置身于一场大学生诗歌运动中,于是它给你带来了一些触动,一些变化,一些回忆,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对于诗歌本身来说,诗歌运动是不重要的。因此我对大学生诗歌运动是不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的说法不置可否,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意义不大。15、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伊甸:投身于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对我来说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鼓动和激励,我更热烈地投身于诗歌写作,更坚定了自己对于诗歌的信念;但这场大学生诗歌运动像潮水一样裹着我向前的时候,我来不及抖掉自己身上的泥沙。我在诗艺和精神上的准备不足,因为发表量太大而带来的虚荣和幻觉,暴露了我的粗糙、浅薄和单调。我必须警告自己:当你被一种潮流裹挟向前的时候,你要设法脱身而出,让自己保持独立、清醒、自省。写作永远是一个人的事情,它跟任何运动无关。写作是一种永恒的自我训练,它与名声无关,与荣誉无关。虽然荣誉看起来是一顶非常美丽的帽子,但它毕竟是一顶帽子,它不是诗歌本身,也不是生命本身。16、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伊甸: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进入嘉兴教育学院做老师。能以大专毕业生的资格做大专学生的老师,也得益于我大学时期在诗歌写作上的微薄成绩。后来教育学院并入嘉兴学院,我就一直在嘉兴学院给学生上现当代文学课和写作课。我以自己对文学的热情煽动起学生对文学的热情。我一直以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鼓励学生。我一共出版过四本诗集,第一本《红帆船》和第二本《在生存的悬崖上》是薄薄的袖珍型诗集,第三本《石头·剪子·布》,第四本《黑暗中的河流》。另有散文集《疼痛和仰望》、《别挡住我的太阳光》,小说集《铁罐》。四本诗集分别出版于年、年、年、年,它们见证着我在诗歌写作上蹒跚向前的步伐。我在不自信、犹豫和纠结中慢慢地进步。唯一有点自信的是,我没有陷在中国诗人年龄越大诗写得越差的魔咒中。当时间把我的生命以出乎意料的速度推向下坡路时,我仍要尽全力把我的诗歌往我所凝望的山上推。我在年出版的《石头·剪子·布》的后记中曾经这样写道:“我的困惑感、孤独感、失落感以及从中孕育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将笼罩我的全部生命和文字,我诗歌的基调必将趋于沉重和忧郁。正如勒内·玛利亚·里尔克的诗句:我爱我生命中的晦冥时刻,它们使我的知觉更加深沉……”此后我的写作正是沿着我给自己确定的方向一路走下去的。我的第五本诗集本来想取名为《恐惧与颤栗》,但这个名字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廓尔的书同名,所以我可能把它改成《颤栗与祈祷》。“祈祷”这个词表示着我在颤栗中对未来、对人性的一点信心。年与学生在一起17、目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诗歌研究者的高度
年7月8日于嘉兴年丰子恺故居年和女儿伊水在一起“致敬中国大学生诗歌三十年”主题书内容征集编撰中,并同步征订,预计于年末上市,敬请期待。联系人:徐向南(白癜风治疗最好的药昆明儿童白癜风医院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qzhduo.com/xzrbrc/143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