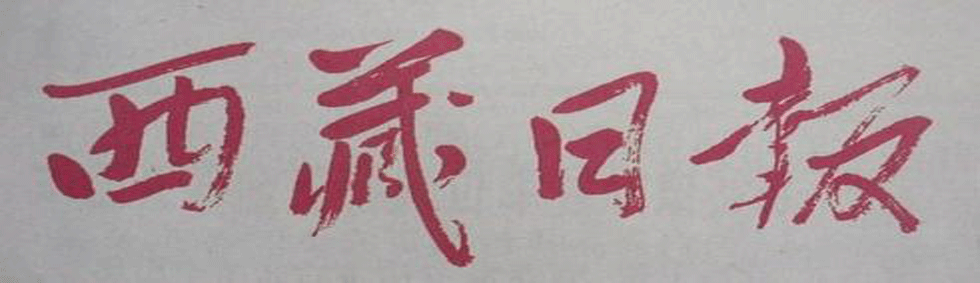
石英矿上的沙娃
大通相金玉
天上的星星都落到地上,闪闪烁烁,闪闪烁烁,变成了绿色的眼睛。对!是眼睛!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在夜的大幕上闪着幽幽的暗光。
是狼!德娃一个激灵挣脱了梦境。刚刚还紧紧瑟缩的身体,一下子忘记了寒冷。睁大惺忪的眼睛,他紧张地观察室外,准确地说是驾驶室室外。
在夜的大海里,德娃的货车只是一叶小舟,它孤零零地停泊在青藏高原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和德娃一样孤苦无依。
一
德娃是沙娃。德娃以前当沙娃是在巷里(淘金洞里)挖含有金子的沙土,现在的德娃在金矿上开货车,但他仍然是个沙娃。这次三老板让德娃开了矿上的车去大通拉煤,没想到车坏到半路上了,修了半天也是白折腾。德娃在又饿又冷中睡去了,醒来时却被狼群包围,德娃觉得自己点子背到家了。以前跟着师傅跑长途货运时听说过,狼群机敏过人,它们知道合围包抄,一但被狼群包围,那就凶多吉少,更何况自己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身边又没有一个帮手。哪怕只有一个人在身边给自己壮壮胆也好啊。他恨恨地想。
德娃的大脑迅速飞转,家里的阿妈、阿大,他们用同一种表情望着自己,仿佛在异口同声地惊呼。这时德娃想到了师傅,记起师傅说过狼群在夜里最害怕亮光……
于是他手忙脚乱地行动起来,货车“呜呜”地吼两声,两道刺眼的灯柱突然亮起,像两把利剑刺穿了黑夜。接着刺耳的喇叭声响起来。德娃想,把车发着,大灯打开,使劲鸣笛,不怕狼群不跑。
德娃一边按着喇叭,一边警惕地望着车外。那些绿色的眼睛立即慌乱起来,“哗”一下,货车周围涌起一大片黑色的波浪,波浪涌动,四散游走。小船般的货车“搁浅”了,大灯映照出前方发亮的柏油路面。
不是狼!德娃狠狠地揉了一下眼睛。
是牦牛!一大群牦牛。已是初秋,山里气候冷了,牦牛们是奔着白天吸收了大量热量的柏油马路来的。
牦牛群被汽车灯光和喇叭声吓跑后,德娃再没能睡着,他像猫一样缩紧身体,还想把脑子也缩起来。可是那无边无际的夜色把他的思想拉得很远。
笃!笃!笃!有东西在敲打驾驶室的车顶。刚刚受到惊吓的德娃,立即又毛骨悚然。天呀!是什么东西在驾驶室顶上。
敲打声越来越大,德娃不敢出声,更不敢伸头去看。这时,德娃居然听到有人在小声叫他的名字。在孤寂黑暗的大山里,这人的声音,反而让他觉得比狼更可怕。
“你是谁?”德娃大着胆子问了一声,声音颤抖。
上面有人回答:“眼镜儿,我是眼镜儿!”
果真像是眼镜儿的声音,德娃大着胆子问了一声:“你真的是眼镜儿?那你说说,眼镜儿的名字叫啥?是回民汉民?”
“我实话是眼镜儿,我是藏民,名字是才秀!德娃!”上面的回答传来。
德娃这才深信自己没有遇到狼,更没有遇到鬼,敲打驾驶室的人是和自己一起在金矿干活的藏民沙娃才秀,外号“眼镜儿”。
“下来!”德娃站在车前,借着天上的星光隐约看到眼镜儿的眼镜片儿在汽车篷布的缝隙里闪着微光。
好一会儿,眼镜儿才从车后跳下车,迅速拉了一把德娃,又跳进了汽车驾驶室。
“干啥呢?大半夜的,又按喇叭,又亮大灯的?”没等德娃上车,眼镜儿已经在车上调侃起了他。
“我还没问你干嘛呢!人不人鬼不鬼的,藏我车上多长时间了?半夜三更,想吓死我啊?”德娃虎着脸跳上车,一把关上了驾驶室的门。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偷了掌柜子的金子,从矿上跑出来了!是不是?”德娃变得严厉起来。
“不是不是,不是!”眼镜儿连连摇手。
“不是?不是你干嘛偷偷摸摸藏到我的车上来了。”
眼镜儿说:“我就是想家,我想回家呗……”
“你跟掌柜子请假了?”
“没。”
“工资领了?”
“没。”
“那你傻呀,傻到家了。”德娃说。
二
挖掘机的大手力大无穷,一把一把地掏出地下的沙土。山顶上,两台大型挖掘机正在削山头。山腰里,四台挖掘机正像蚂蚁一样挖掘着沙土和石块。那些挖掘机挖过的地方,已经接近了“金线”,那是黄金即将显现的地方。一台小型的挖掘机在缓慢地挖掘,每抓起一把沙土,都要小心地装进旁边的皮卡车里,由二老板和大老板的心腹亲自押运去筛洗。洗出来的黄金,统一收藏,再由三个老板按投资比例分红。
德娃的老板是三老板,此时他站在小型挖掘机的边上向德娃招手。德娃赶到三老板跟前,三老板递给德娃一个脸色:“我到顶上去一下,你帮我盯一下。”
挖掘机驾驶室里二老板正在慢慢指挥“眼镜儿”司机才秀挖着前方的沙土。二老板和三老板一起待在这里,互相监督。一旦挖掘机“一爪子”下去,刨出大金块来,那谁也别想吃“独食”。
德娃对于这一带的大山再熟悉不过了。海拔接近米,山谷中间流淌着一条大河。这里远离人间,山间除了青灰色的雾气,便是满山的青草。
眼前这片被大型机械挖掘得只剩下沙土的不毛之地,名为石英矿,实则是三位老板共同开采的岩金矿。为了采得岩金,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三位老板和他们的亲信、招来的司机、亲信再带来的亲信,这些人轮流交叉,互相监督制约,管理着这个以石英矿作幌子的岩金矿。
这座大山里,十几年前就有一批一批开着拖拉机,拉着帐篷、铁锨和镐头来挖金子的沙娃们。在青海民间有这么一个传说:远远有一群人走来了,一个人说:“快看,来了一帮人!”另一人则说:“哪里是人,是一帮沙娃!”
采金人——沙娃,在以前完全没有被当成人。而眼前的岩金矿上,大中小型挖掘机以及货车取代了人力,挖掘机司机、货车司机们都成了沙娃。
德娃作为跟随三老板的司机,充分享有三老板的信任。老板看中的是德娃的机警,还有德娃的话少嘴“牢”。
二老板正在驾驶室里哼着“少年”指挥着挖掘机司机眼镜儿一下一下地挖着前面的沙石。
这里的山已经被挖掘机挖得千疮百孔,植被全部破坏,土层中的石块裸露堆积。温暖的阳光下,德娃远远坐在黑褐色的石堆上,出神地望着挖掘机的机械手臂一下又一下地劳动着,像人的手臂那么灵巧。离挖掘机手臂两米左右,戴白顶帽的马赛哥正比划着指挥要挖掘的位置。
闲暇时,沙娃们总是口无遮拦地嘻嘻哈哈,只有德娃一脸冷漠。时间一长,大家就给他取名“冷胎”。只有眼镜儿说过一句话:“这小伙心里有苦。”大家问为什么?眼镜儿说,你们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嘴角就知道了。
以前自己是个沙娃,给金掌柜挖金字的。现在同样是个沙娃,给金掌柜开车的。德娃暗自思想。
在德娃内心深处埋藏着一段十三年前当沙娃的秘密。与其说是秘密,不如说是痛苦。那时他十五岁。十五岁时的经历,像梦魇一样刻在心里,在机械化采掘黄金的今天,想起那一幕,仍然叫他不寒而栗。对于这段经历,他从来没有告诉过老板,一如老板对他的评价:“嘴很牢。”
三
“停,停!”马赛哥大叫一声。
挖掘机停下了。二老板和司机眼镜儿一起跳下了车。德娃也“噌”一下跑过去。
阳光下,刚刚挖开的沙土中,一具蜷缩着的骸骨正散发白森森刺眼的光。
“有啥大惊小怪的?又不是没见过。”二老板嘟囔着。
马赛哥弯腰举起双手,嘴里咕噜咕噜念起了“嘟哇”。司机“眼镜儿”是藏民,呆呆地看了半天,双手合十,念着“官却送”。
前两天眼镜儿告诉德娃,这样挖下去的话,说不定会挖出以前埋在淘金洞里的沙娃的尸体。没想到眼镜儿一语中的。
以前没有机械设备的时候,金掌柜请来专家测好“金线”的位置就开始掏洞。沙娃们像老鼠一样打洞钻进地下,这些洞倾斜着伸入地下,最深时达二三十米。倾斜着打洞深入为的是及时运送挖出的沙石,也便于沙娃的出入。洞打到“金线”附近时,就变成了直行洞,不再倾斜深入。沙娃们会顺着“金线”向前打洞,一路掏出混着黄金的沙石,运到地面上,再把黄金筛洗出来。
挖金子的过程中遇到塌方被埋在地下的沙娃不计其数,这些离家的受苦人会永远埋在地下。有良心的金掌柜会给他们的家人一定数目的命价赔偿。这些人的家里都是清贫老实的人家,伤心痛哭后,也就不了了之。
眼前的白骨,让德娃想起了十三年前的一幕。
那天的太阳惨白惨白,他像一只老鼠一样被强大的气流推出了淘金洞。还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紧接着一声巨响,身后尘土扬起。
淘金洞就那么突然塌陷了。沙石掩埋了淘金洞,也掩埋了他的四个好兄弟。
“艾萨、尕七儿!”
“旦欠、宝柱儿!”
德娃撕心裂肺地哭喊。他趴到洞口的沙石上疯狂地扒着沙土,十指血肉模糊。德娃不懂,为什么?为什么金掌柜和其他沙娃们只定定地看着他疯狂。他从地上爬起,跪在那些人面前,哀号着求他们救救这四个兄弟。
金掌柜面无表情地看着塌陷的洞口。那一刻,德娃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
后来金掌柜告诉德娃,即使当时大家一起挖,等把那几个人从地下挖出来,他们也早就没命了。之前德娃还听说,一旦人被埋在巷里了,从迷信上说金掌柜也是不会让大家去挖出来的。
心底深处的伤痛一直伴随着他度过了许多年,他不再轻易想起这件事情。一旦想起,他就觉得有一把利爪挠抓自己的心。埋在地下的四个兄弟和德娃一起来到这里当沙娃,尕七儿和艾萨还是德娃的同乡。可是,那场变故让他们四人一齐在德娃眼前消失。许多个夜晚,他听见艾萨的呼唤:“德娃,来救救我们呀!德娃!”他冲出帐篷,外面只有苍白的月色和呼号的风。
直到有一天,德娃远远听见金掌握对大师傅说:“你去买菜的时候,把那个不吃饭也干不下活,一下到巷里就嚎的瘦干棍沙娃拉回家去。”就在那一天,十五岁的德娃结束了自己短暂的沙娃生涯,拖着一身一心的伤痛回了家。
四
青藏高原大山深处的天空,云彩不断变化游走,天空的颜色蓝、灰、白,交叉变换。这样的天空应当映照着绿草如茵的大地才对。可是被挖掘机挖平了的一个又一个的山头它们成为大地裸露的伤口,散发着令人忧伤的褐色光芒。
三老板要去打麻将、睡觉、吃饭、算账……总之,他既不放心二老板带人挖含金子的沙土,也讨厌自己一直呆在挖掘机旁边像狗一样与二老板对望监视。许多时候他就把这监视二老板的任务安排给自己的司机德娃。
午后的阳光明晃晃地笼罩着大地。一对蝴蝶双双飞来,在沙土石块间追逐飞舞,仿佛在寻找曾经开满山坡的绿绒蒿。德娃侧躺在土坡上望了一眼前方正在工作的挖掘机,仿佛驾驶室里的眼镜儿和二老板正扭扯成一团,不知道在做什么。德娃看不太清楚,一下子坐了起来。
挖掘机停了下来,二老板和眼镜儿先后从驾驶室里跳下来向车前面跑。德娃感觉不对,一下从地上跳起来,跑过去看。
马赛哥倒在挖掘机的机器手臂之下,鲜红的血洇红了他的白顶帽,洇红了周围一大片沙土。
“马师!”德娃大叫一声,要往前冲。二老板一把拉住德娃,向他递了一个眼色,压低声音说:“已经下场(死)了。”
“啊!可是……”德娃焦急地看了一眼歪歪地躺在一边的马赛哥,那毕竟是一条命啊。
“不就是一个沙娃吗?一条命价才多少!哼哼哼……”二老板一阵冷笑,“还想吃独食儿,自己找死!”二老板说着一些咒骂的话语,这让德娃摸不着头脑。二老板一把将德娃扯到一边,不许德娃靠近马赛哥。
看了看二老板阴森诡谲的表情,德娃又看一眼眼镜儿,他正面如死灰,瑟瑟发抖。
“我让你俩看看吃独食的沙娃下场!”二老板迅速上车开动挖掘机。很快,挖掘机在马赛哥身边一铲挖了下去,机器手臂灵巧地把马赛哥连同身边的泥土一起铲起来。马赛哥被鲜血染红的身体被机器手慢慢举起来,越举越高……
站在一边的眼镜儿越发抖得厉害了,德娃刚想扶住他的胳膊,他便晕倒在地。
后来二老板一再厉色告诫德娃,马赛哥自己不小心被挖掘机挖下来的沙土埋住了,等二老板、眼镜儿、德娃发现时已经死了,任何人问起,都必须这么说。
五
“德娃,你听我给你说。”眼镜儿变得异常冷静,“我要回家,马上回西宁的家,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越快越好。你必须马上送我走,离开这里,去西宁。”眼镜儿望着德娃,镜片后面一双小眼睛焦急万分。
“你不是化隆的藏民吗?家怎么跑到西宁去了?西宁城里的人还会跑到大山里当沙娃?”德娃笑了一声。
“我家里有万分紧急的事,我必须马上回家。”眼镜儿蠕动干裂的嘴唇说。
“一个沙娃要回家,没带钱,也没带金子,还是从矿上跑出来的,还要跑到西宁城里去?”德娃冷冷地说道。
“弟兄,如果你不马上送我走,矿上的人一旦追上我,我的命就没了,你的命也悬。”眼镜儿的话如铁板钉钉,一字一句钉得德娃后背渗出了冷汗。
“你知道马赛哥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金矿为什么对外叫石英矿吗?你知道金矿的大老板是什么人吗?”眼镜儿的这些个问题也是德娃平时想过的,德娃摇摇头。
“我除了带着这个东西,啥也没带。”眼镜儿小心地把一个小东西拿到德娃眼前。
“照相机?”德娃问道。
“比照相机更金贵的东西。”说着,眼镜儿打开那机子上的按扭,机子的显示屏上赫然出现了矿上的马赛哥。山坡最低处,被机器翻挖得一片狼藉的黑色土石背景下,戴着白顶帽的马赛哥背对镜头,蹲在地上,正认真地看着手里的什么东西,紧接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挖掘机的手臂突然就落了下来,直击马赛哥的头顶,马赛哥无力地倒了下去……
“你?你是说,马赛哥是被二老板故意砸死的……为什么?为啥要这么做?”德娃觉得自己颤抖起来。
“二老板说他看到马赛哥从地上捡到金子了。一块花生米大的金子,说马赛哥想吃独食……”
“后来,二老板给我看过一块金子,说是从马赛哥身上拿到的。”说着,眼镜儿动了半天那个小机子,从里面翻出一张照片来,上面真的有一块花生米大小的金子。“就是这块,二老板拿给我看的那块金子。说是马赛哥偷藏在身上的。”眼镜儿指着金子说。
“你不是沙娃!”德娃盯着眼镜儿的眼睛,手指着眼镜儿手中的小机器。
“我是沙娃,一个有良心的沙娃!”眼镜儿说。
“不不,你不是沙娃。我知道了。如果你不愿意说,我便也不问了,你放心,天一亮,我就送你出山。”德娃说。
六
黎明时分,德娃带着眼镜儿离开货车,进入了密林。
德娃告诉眼镜儿离这里不远处有一条便道,汽车过不去,但人勉强可以过去。那条小路直通拉加镇,从拉加镇就有直达县城的汽车,从县城可以坐到西宁的公交车。德娃说这条路是他十五岁挖金子时走过的,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眼镜儿说,只要能走到可以打电话的地方,就万事大吉了。他把那个小机器用布包好,放到贴身的衣服里面,和德娃一起出发了。
行走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
“德娃,你听我说,这挖金子的活儿你是干不下去了,你要另找一个挣钱的活儿。”眼镜儿说。
“城里盖楼房的工地我去过了,可我没啥技术,只能当个小工,小工工资低,挣不了钱。”德娃说。
“回家种地……种有特色、无污染的蔬菜,比方西兰花、甘蓝之类的。”眼镜儿说。
德娃说:“家里哪有地哩?原先有两亩地,前年被政府征用,那里成了工业园了。”
眼镜一听“哦”了一声,半天不吭声。后来又有些兴奋地说:“那你买辆货车,跑运输——征地款能买辆车吧?”德娃说:“买啥车?去年阿大得了肠梗阻住院手术就花了两三万多。阿妈又被车撞了,车主儿还跑了,腿也折了,肋巴也断了,动手术打钢板又是好几万。没有多少征地款了,阿大说不能再花了,要存着给我娶媳妇。”
眼镜儿听后,摇了下头。走了一段路,眼镜儿突然说:“我知道的事太多,矿上的人发现我不见了,一定会找的,尤其是二老板,在矿上的时候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德娃说“放心,他们车来车往,不知道这条小路。”
“好吧好吧,只要你送我这个沙娃回家,我一定找辆车回来,给你这个开车的沙娃送来备胎。”眼镜儿说。
两个人忍受辘辘饥肠步行了七八公里,穿过了大半个山林。从长满勾头草的山坡,转过布满林木的阴山,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小路若隐若现伸向山外。德娃指着远处的小路说:“眼镜儿,剩下的路好走多了。我得赶紧回去,说不定他们在追你,如果看到车上没有我,我也说不清了。”
眼镜儿点点头,说:“也是,你赶紧回。”
七
德娃赶到货车时,已经是下午了。远远地看到有几个人在汽车周围徘徊。
“尕德儿!上哪儿去了?”二老板眯缝着眼睛出现在车门前。
“老板让我去拉煤,结果,结果我的车坏到这儿了。”德娃说。
“车坏到这里,你不修车,跑到哪里去了啊?”二老板掏出一把瓜子儿,嗑着。
“修了,车胎爆了。把备胎拿出来装上一看,唉,备胎里没气啊,也是烂的。我只好等着拦一辆车回矿上取个备胎,或者带着烂车胎去哪里补好,再回来开车。只是,我一直没有等到过路的车啊。”此时的德娃觉得又累又饿,眼前直冒金星,他顺势靠在车上。
二老板默不作声地盯着德娃。盯着,盯着,他走过来一把撕住德娃胸前的衣服,“你在这里,那眼镜儿上哪里去了?”
“眼镜儿?”德娃的身体向后趄了一下,“眼镜儿,我没看见!”
“你们刚刚不是在一块儿吗?”二老板眯起细长的眼睛,一脚踢到德娃的腿上。
“不是看在你是老三的人的份上,我不打死你个穷鬼沙娃!”二老板诅咒着,拳脚雨点般落在德娃身上。
“别打了,别打了,我说,我说。”德娃哀号着。
“我看到眼镜儿了,可他不让我告诉你们。”德娃擦了一下嘴角的血,一屁股坐在地上。
“看,你早点说不就对了?”二老板凑到德娃跟前。“快点说,那个眼镜儿在哪儿?”
“他回家去了。”德娃慢慢地说。
“啥?回家去了?”二老板将信将疑地问。
“嗯,昨天下午我的车坏在这里的时候,他从车上跳下来,说是从矿上跑出来了。看我的车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他说他得先走,就自己走了。”德娃继续慢慢地说。
“自己走了?坐的什么车?往哪里走了?”二老板趴下身子问德娃。
“没有车,他是步行的,一直往前走了,一直往前……”德娃抬起手指着前面的公路,公路正温柔地伸向前方,弯弯曲曲,闪着清亮的光。
八
德娃梦见阿大阿妈站在家门口张望,远远看到他们,德娃高兴地叫起来。刚要开口,忽然就醒了。原来自己还躺在公路边,周围一片寂静,只有他的汽车静静地陪伴着他。天色已经完全暗了,黑色的大山的重影,一层层压迫下来,冷风嗖嗖,透着刺骨的凉意。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又挨了一顿打,德娃觉得身体轻飘飘地像随时会飞离地面。
德娃心里暗自庆幸:二老板的人已经顺着公路开车去追眼镜儿了。顺着这条公路一路下去,离实际上眼镜儿去的海黄县拉加镇至少有二百公里。二老板根本不可能找到眼镜儿!
德娃摸索着慢慢爬起来,扶着汽车一步一步走到车门前打开车门,挪进了驾驶室。
“德娃,你知道矿上的大老板是谁吗?”
“不知道。”
“不想知道?”
“你不说,我就不想知道。”
德娃静静地躺在驾驶室的车座上,回想自己抄小道送眼镜儿离开时,两个人在路上的对话。
“这里的水深得很,据说大老板是省上的一个大官儿。有了他,二老板和三老板才敢打着石英矿的幌子,开岩金矿!”眼镜儿说。
“哦,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大老板。光知道矿上有四个人是大老板派来的心腹。”德娃说。
“你知道矿上那座山被挖掉了多少米吗?”
“有二、三十米吧。”德娃说,“以前山上长满了草,开满了花儿,清秀得很,现在那些挖掘机把山削平了,怪可惜的。”
“那叫破坏生态!那里的植物、动物都没有了家,这里的气候都会受影响的。一刮风就飞沙走石,一下雨,不是滑坡,就是泥石流。这里海拔高,生态脆弱,今后就算想恢复,也恢复不上呀。”眼镜儿叹了一口气。
“你实话是个秀才,懂的真多。我可没有你想的多。”德娃随手摘下几条树枝编了一个凉圈扣到眼镜儿头上。
眼镜儿说:“沙娃不好当,这么的沙娃也当不得。把大山挖得千疮百孔,简直就是犯罪啊!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
恍恍惚惚,黑色的大山变得面目狰狞,像巨大的怪兽虎视眈眈地看着德娃。德娃想,前面马赛哥死了,后面自己的车又坏了,挨饿、受冻、挨打,莫非老天爷真的开始惩罚大家了?
“我不想当沙娃。”德娃喃喃地说。
九
“德娃!德娃!快醒醒。”矇眬中,德娃听到眼镜儿呼唤自己的声音。
“你怎么又回来了?二老板去追你了……快……”德娃说。
“二老板已经让公安局给抓住了。你快起来,你看,我给你泡方便面了。”眼镜儿微笑着向德娃递来一桶热气腾腾的方便面。
“二老板真的被抓了?”德娃忍着浑身的酸痛慢慢坐起来,皱着眉头问。抬头时,发现天早已经大亮了,倒车镜上反射着晃眼的阳光,大地洁净又明亮。
“我现在让人给你的汽车换备胎。你先吃点东西,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说。”
眼镜带来的人很快换上了备胎。德娃吃了热热的方便面,休息了一阵子,觉得又来了力气。
眼镜儿告诉德娃,二老板已经被警察抓住了,省城里的大老板也被控制起来了,石英矿马上要被关闭了。
德娃吃惊地望着眼镜儿,喃喃地说:“那我上哪里去呀?我答应三老板去给矿上拉煤的。”
“弟兄,回家好好过日子吧,别当沙娃了。三老板也已经不在矿上了,你不要再回去了。”眼镜儿说。
“如果不是你,我肯定让二老板给害死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弟兄,以后有事就来西宁找我。”眼镜儿掏出一个小纸片给他。德娃看了一眼,上面写的是“《平海日报》记者:才秀”,下面是一排电话号码。
告别了眼镜儿,德娃开车出发。他决定把车开去还给三老板,然后回家。当天下午,德娃赶到了三老板的老家,把车停放到他家门口,把车钥匙交给了三老板的儿子。
“阿大,石英矿上出了点事,我再不干了,我现在去坐车,明天中午就能到家。”在长途汽车站的公共电话厅里,德娃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娃娃,跟着大老板好好挣钱,挣了钱还要娶媳妇哩,老想往家里跑,没出息啊!你回来干啥?”阿大的声音有些愠怒。
德娃拿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土地被征用了,自己又没有文化,他一时想不出回去还能干些啥。
作者简介:
相金玉,汉族,毕业于青海省司法警官学校。在《青海湖》《青海日报》《西藏文学》《雪莲》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若干篇。系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大通县委宣传部。
赞赏
人赞赏
专业治白癜风全国青少年白癜风公益援助